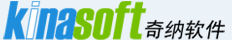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须五根手指——品牌、技术、价格、规模和服务——握成拳头才是实力。
十年做好一件事,懂得选择懂得放弃,坚持一夫一妻制。
做产品就像养小孩子,要养就要养一个思想品德好的孩子,不能养一个坏孩子。
企业家的决策不能出错。战术可以容许失误,但战略只有一个,你要出了差错就全输了。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形成一种抗风险的能力和防范风险的意识。企业要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就先做一些准备。
格兰仕就相当于一个美食城,有过桥米线、拉面、川菜、鲁菜等等,来者不拒,你可以带灶具过来,也可以不带灶具过来。格兰仕是全世界的生产车间,将合作伙伴多余的生产能力挖掘出来,形成新的竞争力,从而提高我们本身的生产力水平。
选择上海卖出第一台微波炉
在各方面很薄弱的情况下,格兰仕不可能进行全国性的渠道建设,因为既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可行性。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以后,梁庆德选定了上海作为切入点。选定上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上海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产品在这个城市上柜有一种示范性的作用;其次,上海的消费者是整个中国最挑剔的消费者,征服了上海的消费者,就有了征服全国的底气;最后,上海的消费者是最讲时髦的,比较前卫的产品要在全国打开局面就先要从上海打开局面,在整个中国大众对微波炉还未了解的情况下,在上海上柜也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以当时国有百货公司的“老大哥”作风,一个默默无闻小乡镇企业想要进去,其难度可想而知。如今格兰仕的副总经理陈曙明是格兰仕的第一代业务员,也是第一个打进上海的业务员。他跑到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南京路,向当时号称“中国第一店”的百货公司推介格兰仕的微波炉。一开始百货公司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陈曙明天天碰壁,但仍然天天去,跟百货公司的人交朋友,帮人家干活,慢慢地感动了人家。百货公司的人终于勉强同意让他的微波炉上柜试一试,卖不掉就拿走。花了三天时间,陈曙明终于把格兰仕的第一台微波炉给卖了出去。卖出去以后,打电话回来,说了声“德叔”就哭了。
民营企业草创之初的艰难,从这一台微波炉上可见一斑。而正是这样千千万万个敢于碰壁的民企员工,为中国的民企在一片荒芜中开垦出一条道路。
天灾的洗礼
对格兰仕来说,1994年是这个企业无法磨灭的记忆。这一年,广东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格兰仕在防洪的过程中一个管涌没堵好,就把整个厂区淹成一片汪洋,积水将近半米深。在外部,竞争对手幸灾乐祸;在内部,工厂员工人心惶惶。企业内外都存在一种“格兰仕不行了”的声音。
这个时刻也正是判断一个企业家决断力的紧要关头。梁庆德在洪水暂缓之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借钱给每一个员工发两个月的工资,并称,愿意留下来的在工厂等待复工,不愿意留下来的自行回家。这项决策感动了许多原本以为工厂会停发工资的员工,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个企业不能撑过这一关,不但格兰仕倒闭,他本人也要负上巨额债务。
由于工资提前预支,工厂生产员工的人心很快稳定下来,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微妙心理,整个厂区工作热情高涨。这种情形不但发生在生产一线,而且连锁反应式地感染了格兰仕在销售线上的业务员和经销商。
“有些销售代理商不但没有离开格兰仕,反而提前打款给我们。而在市场上的业务员看到后方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在坚持抗洪救灾,恢复生产,前线的人也被感到了,一天当三天用。1994年本来是一个灾年,但是在销售上,反而成为格兰仕的丰收年。”
这一年,格兰仕的销售增长达到50%以上。
“价格屠夫”的背后绝决
有一次,梁庆德在广州的友谊商场发现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妇:在商场徘徊良久,打量着一台微波炉,但来来回回看了三次都没有买。梁庆德很奇怪,上前跟他们搭话。这对年轻夫妇说:“这个产品很好,但价格太高。如果我要买一台微波炉,那我们两口子半年的工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虽然很想买,但觉得还是有点奢侈。”
这段话打动了梁庆德的市场神经。如果按照微波炉当时的价格和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微波炉这种产品将永远不会进入平民家庭。“产品不能进入百姓家庭,就意味着它的容量很小,市场面很窄,这样我的企业将会永远被这个市场容量限制住,没有做大的机会。”
当时,格兰仕出了微波炉以外,羽绒制品的生产线并没有停掉。从广州回到顺德以后,他在工厂开了一次会,决定把轻纺生产线全部卖掉,全力以赴把微波炉这一块的规模做大,以规模的增大来降低成本。在这样的决断下,格兰仕砍掉了轻纺部门,把所有的资源向微波炉集中。“只有规模做大才能把成本降下来。把成本降下来,消费者才能在价格符合他的需求的情况下踊跃去购买。像现在汽车和房子一样,不是老百姓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他们消费不起,因此他们便持币待购。当时的微波炉也是这种情况。”
凭直觉取胜
做这样的决断,要面临比在水灾期间发两个月的工资更大的压力。一旦微波炉这一块做坏了,整个企业也就危险了,这是一种背水一战的行为。在格兰仕内部,当时也不乏反对的声音。但梁庆德终于拍板了。
要承担很大的风险。1996年,“总成本领先”的概念基本上还游荡在中国的国门之外。梁庆德的这项决策,只是基于民营企业家对市场的直觉和判断。
要把资金往一个地方集中→规模上去了→成本降下来→市场上微波炉降价→降价了以后把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变成消费行为,把市场的消费潜能变成消费事实→市场容量增大→拉动销售→企业资金回流,企业规模再次扩大→成本再次下降……这个简单的逻辑,引起了中国微波炉一波又一波的价格战。
“价格战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策略,但为什么能做好的企业寥寥无几?因为这个看似很简单的策略如果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系统的工程来做,而只是在下游降价的话,最终将导致利润的趋薄甚至亏本。你必须把规模做大,让自己得以开发核心产品,降低成本。所以价格战的背后是一个价值链条,你必须最大可能地掌控这个价值链条,你才能拥有别人所没有的降价空间。”
中国民营企业早期之所以成功,很多时候靠的是领航者的敏锐直觉。对他们而言,总是行动先于理论。实际上,管理学上的成功理论也不过是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在很多时候,左右市场竞争结果的就是决策速度:等到21世纪,“成本领先”等理论进入中国为大多数企业家所接受的时候,市场早已经被梁庆德们瓜分一空了。 |